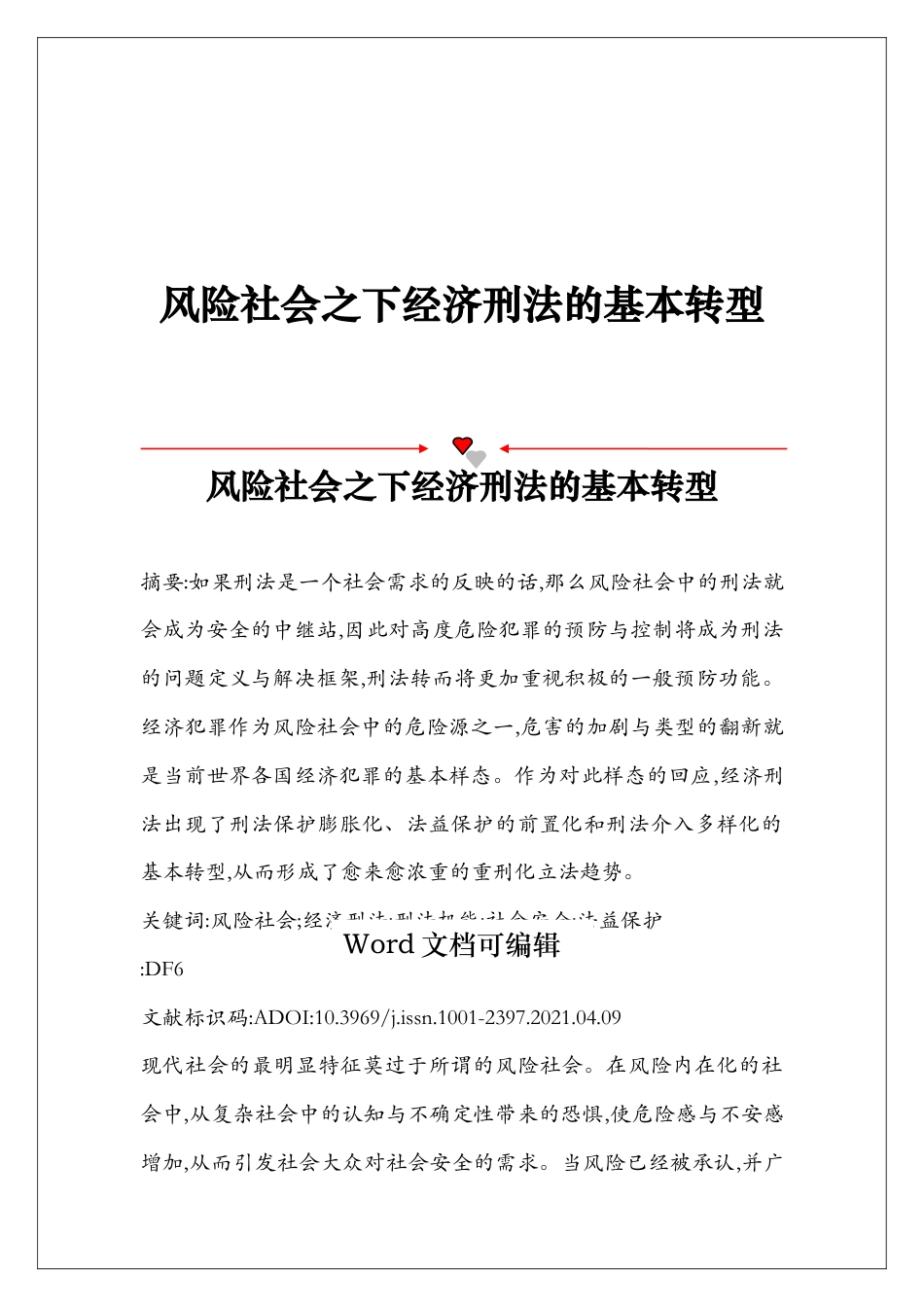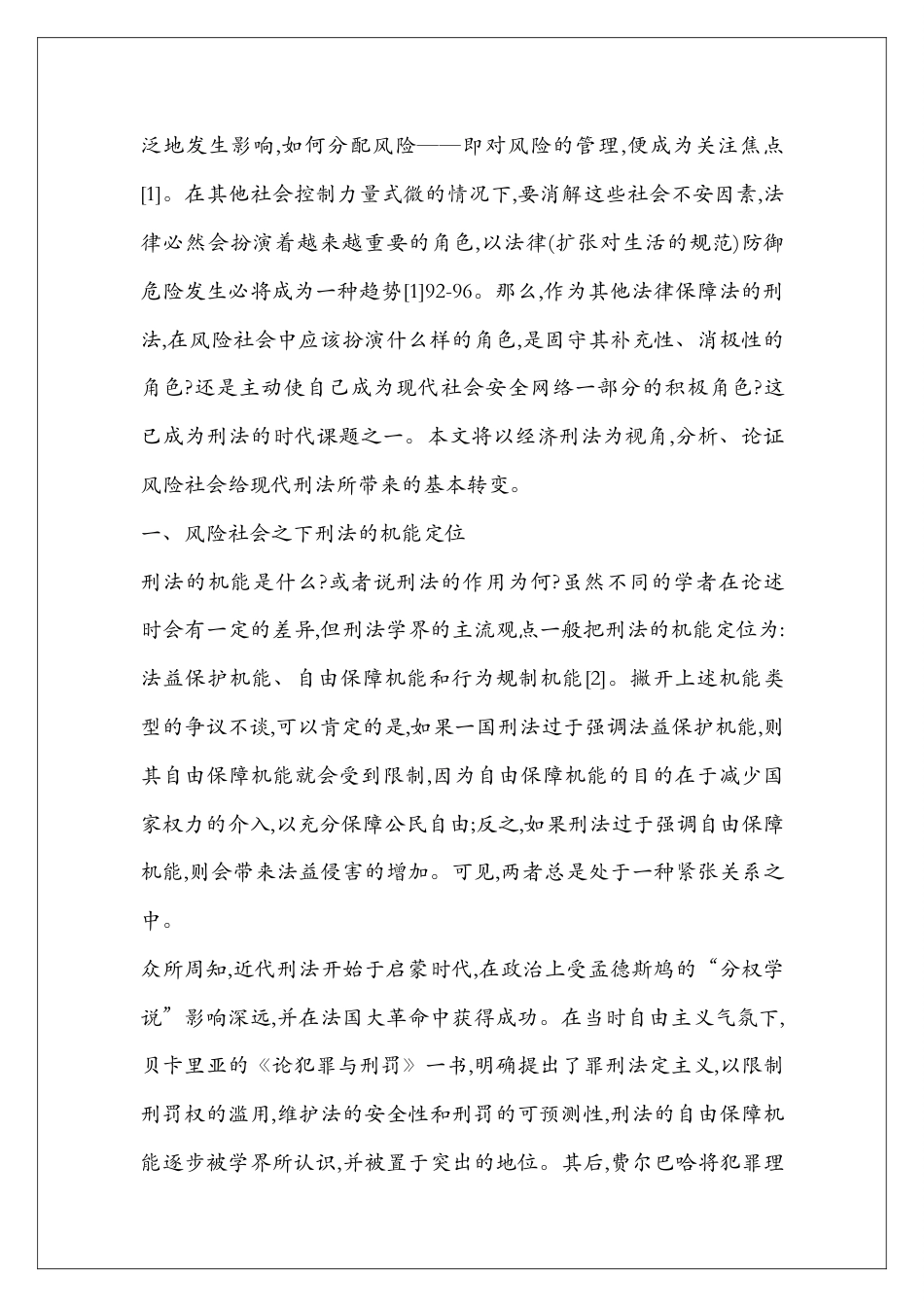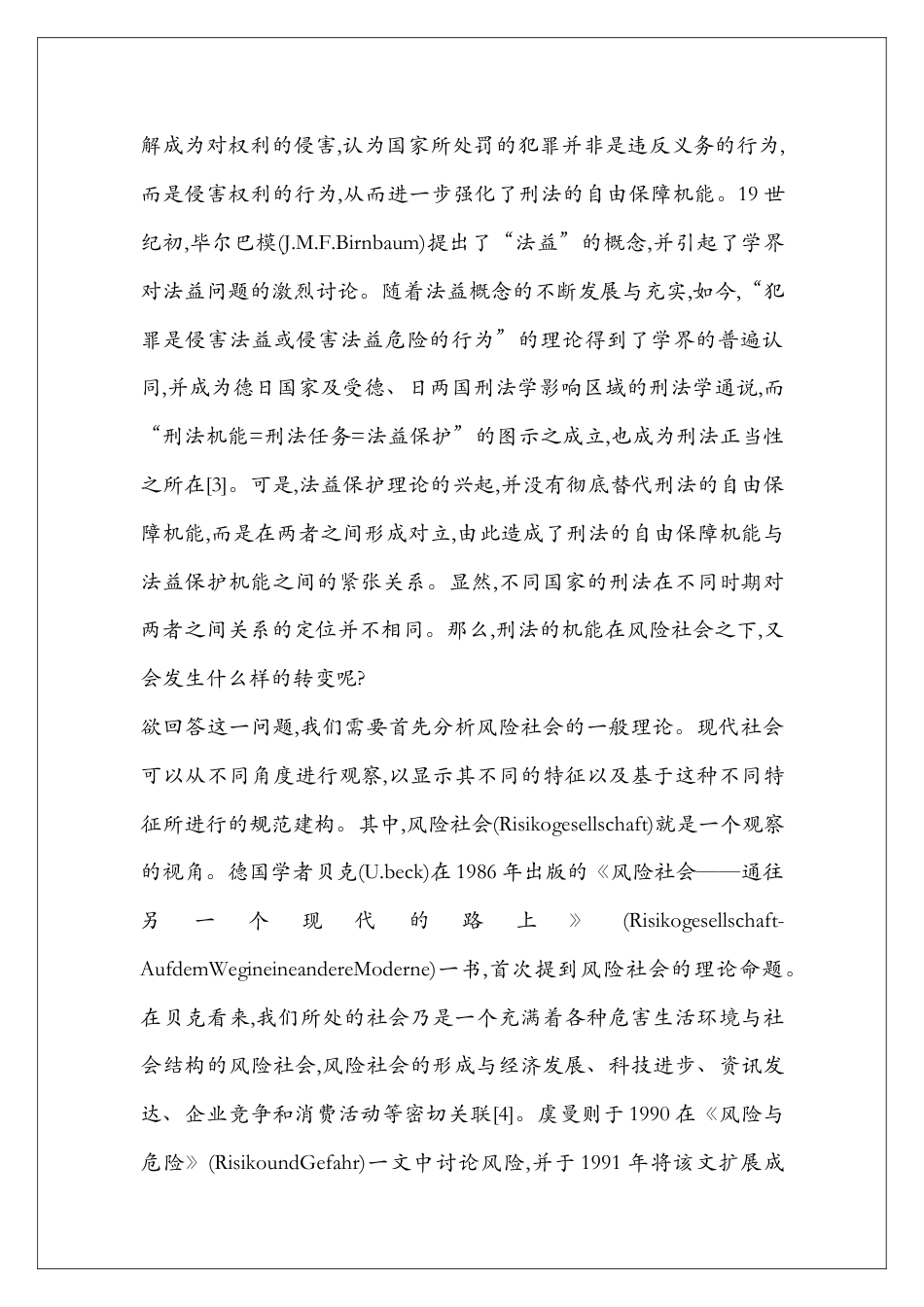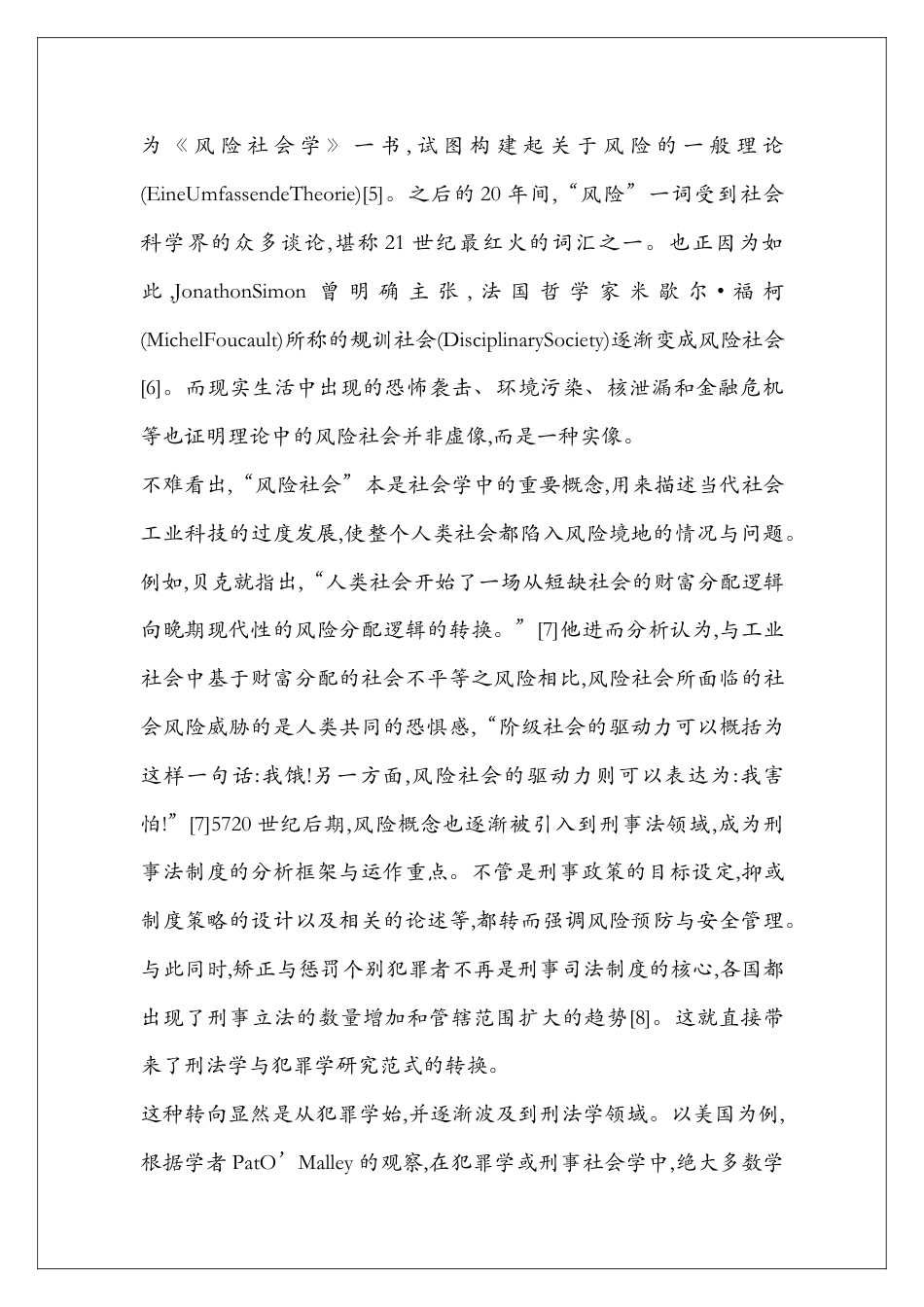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基本转型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基本转型摘要:如果刑法是一个社会需求的反映的话,那么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就会成为安全的中继站,因此对高度危险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将成为刑法的问题定义与解决框架,刑法转而将更加重视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经济犯罪作为风险社会中的危险源之一,危害的加剧与类型的翻新就是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犯罪的基本样态。作为对此样态的回应,经济刑法出现了刑法保护膨胀化、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和刑法介入多样化的基本转型,从而形成了愈来愈浓重的重刑化立法趋势。关键词:风险社会;经济刑法;刑法机能;社会安全;法益保护:DF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1.04.09现代社会的最明显特征莫过于所谓的风险社会。在风险内在化的社会中,从复杂社会中的认知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使危险感与不安感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大众对社会安全的需求。当风险已经被承认,并广Word文档可编辑泛地发生影响,如何分配风险——即对风险的管理,便成为关注焦点[1]。在其他社会控制力量式微的情况下,要消解这些社会不安因素,法律必然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法律(扩张对生活的规范)防御危险发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1]92-96。那么,作为其他法律保障法的刑法,在风险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固守其补充性、消极性的角色?还是主动使自己成为现代社会安全网络一部分的积极角色?这已成为刑法的时代课题之一。本文将以经济刑法为视角,分析、论证风险社会给现代刑法所带来的基本转变。一、风险社会之下刑法的机能定位刑法的机能是什么?或者说刑法的作用为何?虽然不同的学者在论述时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把刑法的机能定位为:法益保护机能、自由保障机能和行为规制机能[2]。撇开上述机能类型的争议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国刑法过于强调法益保护机能,则其自由保障机能就会受到限制,因为自由保障机能的目的在于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以充分保障公民自由;反之,如果刑法过于强调自由保障机能,则会带来法益侵害的增加。可见,两者总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众所周知,近代刑法开始于启蒙时代,在政治上受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影响深远,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成功。在当时自由主义气氛下,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主义,以限制刑罚权的滥用,维护法的安全性和刑罚的可预测性,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逐步被学界所认识,并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其后,费尔巴哈将犯罪理解成为对权利的侵害,认为国家所处罚的犯罪并非是违反义务的行为,而是侵害权利的行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19世纪初,毕尔巴模(J.M.F.Birnbaum)提出了“法益”的概念,并引起了学界对法益问题的激烈讨论。随着法益概念的不断发展与充实,如今,“犯罪是侵害法益或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的理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德日国家及受德、日两国刑法学影响区域的刑法学通说,而“刑法机能=刑法任务=法益保护”的图示之成立,也成为刑法正当性之所在[3]。可是,法益保护理论的兴起,并没有彻底替代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而是在两者之间形成对立,由此造成了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不同国家的刑法在不同时期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定位并不相同。那么,刑法的机能在风险社会之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欲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分析风险社会的一般理论。现代社会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以显示其不同的特征以及基于这种不同特征所进行的规范建构。其中,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就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德国学者贝克(U.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Risi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一书,首次提到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在贝克看来,我们所处的社会乃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危害生活环境与社会结构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资讯发达、企业竞争和消费活动等密切关联[4]。虞曼则于1990在《风险与危险》(RisikoundGefahr)一文中讨论风险,并于1991年将该文扩展成为《风险社会学》一书,试图构建起关于风险的一般理论(EineUmfassendeTheorie)[5]。之后的20年间,“风险”一词受到社...